
中国人很早就提出“书画同源”,对于此,历代都有不同的解释,但不论如何解释,都离不开中国绘画与书法之间密切的关系,两者的产生和发展相辅相成。作为20世纪开宗立派的一代绘画大师,李可染在书法上同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,而且他的书法与绘画密不可分。
可染先生少年时代便专力摹写“赵体”,为他奠定了扎实的书法功底,但不久他便悟到这种书体易失之流滑、柔媚而少骨力,因此,中年以后,可染先生以极大的毅力矫正自己的书写习惯。进入国立杭州艺专后,可染先生曾改学西画。抗战期间在重庆再次开始精研传统,创作了大量减笔人物画和山水画。当时他的用笔迅疾,线条流畅而率性,虽没有独立的书法作品存世,但从画中题款那潇洒流利的行草书来看,用笔率真,强调结构的趣味,和画面有机地结合起来。抗战胜利后,可染先生到北京师从齐白石,随侍齐师十年,他并没有直接学习齐白石的画,而是学到了齐白石绘画、书法最关键的一个字,“慢”。50年代,为改革中国画,可染先生多次外出写生,在潜心钻研、努力探索新的山水画语言的同时,他开始抛弃了早年那些率意奔放的行草书,更多地以楷书题画,他的绘画和书法用笔都慢下来了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在“文革”特殊的时期里,他反复练习平直得近乎刻板的“酱当体”,使他的书法在“慢”中获得了几分“拙”的意趣,既有气势,又非常凝重、拙朴。60、70年代初期,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,可染先生写了大量的毛主席诗词,如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、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、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、《沁园春·雪》等,多以汉隶《张迁碑》掺以魏碑笔意,整体显得凝重、遒劲,留下了很深的时代印记。到了70年代中后期,可染先生的书艺进入更高更成熟的阶段,他为友人与学生的题字中经常出现如“金铁烟云”“龙跃天门、虎卧凤阁”一类句子,他立足碑派体系而又广收博取,着重理性分析而又注重神韵,把一丝不苟的匠心安排寄托在情寄八荒的襟怀之中,将别出心裁的构思安顿在严格的法度之中。进入80年代,由于可染先生在国画界崇高的地位,社会应酬增多,找他题字的单位和个人非常多,这一时期他的书法作品内容更多涉及唐诗、名言、楹联,为各地的报纸杂志、名人故居题字,如《中国日报》、《深圳美术馆》、《丰子恺故居》等,包括《美术家》、《江苏画刊》、《迎春花》等重要艺术类刊物、著作题签。布局构图必经营再三,落笔即极具妙趣。作为齐白石的弟子,他为齐白石作品出版物题签有:《齐白石三百石印》、《齐白石手批师生印》、《齐白石精品画选》等,精心布局中糅合着隶篆之意,缓慢运笔中寄托着对恩师怀念之情。在大量的牌匾题写中,李可染为家乡徐州题写了《我爱家乡徐州》、《徐州双拥陈列馆》、《快哉亭公园》、《戏马台》等,为了让上门求字单位或个人制作牌匾方便,可染先生大都会题写一横一竖两幅,字里行间寄托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。字体从拙朴中透露出灵动,个人面貌也日益突出。到了80年代中晚期,又以印语入书法,书写了《实者慧》、《白发学童》、《所要者魂》、《峰高无坦途》等,充分体现他独特的人生观与艺术观。
可以说,可染先生的书法经历过一种看似刻板的演变,最终脱胎换骨,从率意流畅,到慢,再到朴拙。从改革开放到他去世的10年间,他的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又有一种新的升华,笔墨的成熟,书法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他的书法强调的不再是早年的那种结构美,而是包含有“丑”的意味,但不是一般的“丑书”,强调的是一种“拙”的大美,正如他说的那种“白发学童”,即儿童般的稚拙,凝重而力透纸背的线条,让人自然想到历代书法家所苦苦追求的“屋漏痕”“锥画沙”。可染先生书风从率真演变到质朴再到古拙,同时也是一种审美追求的变化,这种审美的变化正好符合中国书法对境界的要求,达到了孙过庭所说的“人书俱老”的境界。不同阶段的追求是偶然和必然的一种转变,这种转变是他认识的升华,也是他笔墨功夫锻炼的必然。通过对可染先生书法发展的几个阶段的研究,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他在书法上取得的成就,也能借此认识和研究其中的规律。
可染先生的书法在中国绘画史、书法史中都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风格,可以说是独树一帜。他的书法中独有的“拙”超出了清末何绍基、伊秉绶。同时,他的“拙”中又有中国文人的书卷气,很重、很厚,有时显得很满,但因为有内在的书卷气,以及他在中国文化滋养中形成的那种境界,所以他的书法中没有燥气、习气、黑气。
最新文章
推荐文章
热门文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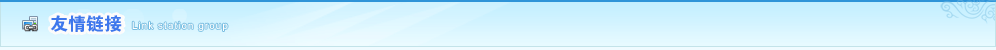
365838.com 电话:0371-66930016 67170207 豫ICP备08101441号